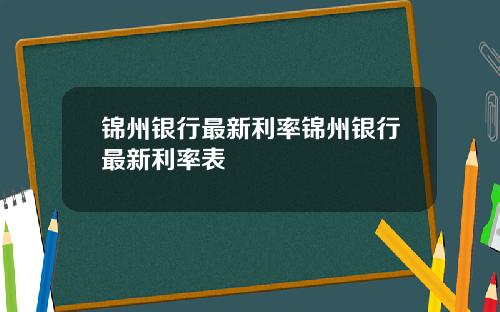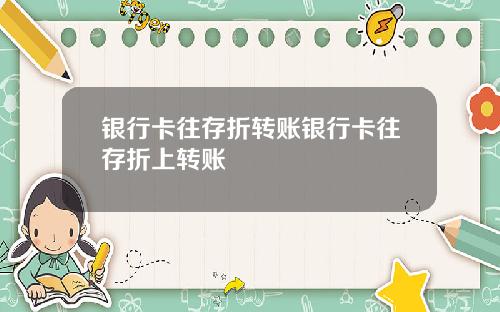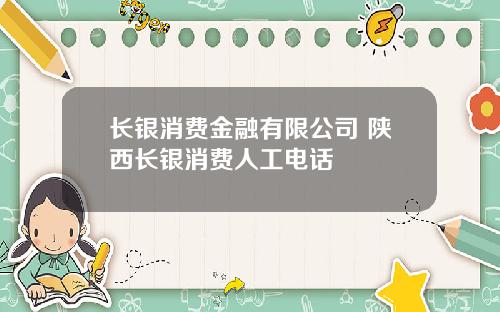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出多轮量化宽松政策以应对金融危机。对比美国在危机前后十年间的通货膨胀情况可以发现,唯有2011年通货膨胀率超过3%,全球通货膨胀也并未因量化宽松政策而大幅回升。
2020年3月底,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以及美国股票市场的爆跌,美联储开启了无限制的量化宽松举措,自此,美国通货膨胀指数隐含的通货膨胀预期开始攀升。在全球新一轮的宽松刺激政策下,消失的通货膨胀未来是否会卷土重来,成为投资者关心的话题。
全球通货膨胀消失的原因
针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通货膨胀消失的原因,简要总结,主要是以下方面原因。
●货币乘数的下降以及资产价格对流动性的吸纳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迅速扩张,由之前的不到1万亿美元扩张到最高的接近4.5万亿美元,但美国的通货膨胀不但没有上行,反而出现了下行。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大幅扩张导致美国基础货币增速大幅上升,但广义货币增速M2一直保持相对低迷,只有2010-2012年出现回升,此后震荡下行。2012年初,美国M2增速达到危机后的最高水平10%,之后持续下行,最低为2018年的3.3%。导致美国基础货币增速和M2增速背离的主要因素在于货币乘数的下降。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货币乘数大幅下降,由危机前接近9的水平下降到危机后的平均3.7。美联储虽然有能力扩张基础货币,但无法决定广义货币增速,货币乘数的扩张源自商业银行通过信贷行为进行货币创造,这和整个实体经济的需求存在紧密联系。
那么,美联储投放的流动性都去哪里了?
其一,很大一部分流动性转变为商业银行存放在美联储的超额准备金。2008年8月,美国的超额准备金不足20亿美元,占美联储总负债的比例仅为0.2%;2014年4月,美国的超额准备金为2.7万亿美元,占美联储总负债的比例高达62%。美国超额准备金开始下降的时点与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的时点基本一致,这意味着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投放的流动性,大多沉淀在银行间市场,并没有形成实际的信贷。其二,由于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较弱,流动性难以进入实体经济,在金融系统空转,大量流入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这是美国股市十年长牛的重要基础。
●压制通货膨胀的结构性因素
除上述因素外,导致全球性通货膨胀消失还存在结构性因素。
一是全球贫富差距扩大,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对整体消费产生一定的抑制。
货币政策作为逆周期调控的手段,具有财富再分配效应,主要通过资产价格渠道发挥作用。美国股市十年牛市,富人的财产性收入上涨较快,普通人拥有的金融资产较少,而且在实体经济长期低迷的环境下,可支配收入也难以大幅增长,这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富人的财产性收入虽然增长较快,但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这不利于消费的增长。
二是全球化叠加科技的迅速传播发展,整体压低了全球一般商品的生产成本,这对普通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形成压制。
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化仍在迅速发展,普通商品在比较优势下实现精细化分工,从而导致生产成本最小化。此外,科技在全球的迅速传播发展,一定程度提高了普通商品的生产效率。全球化叠加科技的迅速传播发展,整体压低了全球一般商品的生产成本,这会对普通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形成压制。
全球通货膨胀未来如何?
●此次政策刺激与以往不同
面对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美联储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无限量化宽松,规模与速度都超过了之前的力度,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也由疫情之前的4万亿美元迅速膨胀到目前的7万亿美元。
与前三次操作不同的是,疫情期间的资产购买主要为国债(占比为67.3%),并新增了一般贷款、工资保障计划流动性贷款、中产阶级贷款计划、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信用贷款投资组合净值,而这些操作更有利于资金投向实体经济。这也表现为M2增速的快速攀升、超额准备金规模以及其占美联储负债的比例虽然有所上升,但幅度非常有限,远远低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使用量化宽松期间,这也说明本次疫情后的量化宽松操作效率更高,对于资金的空转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此外,本次疫情期间,财政政策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弥补了居民和企业由于封锁隔离导致的收入下降,尤其是对于居民而言,部分失业救助甚至超过了正常时期的收入水平。
债务高企的背景下,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乘数下降背后的原因是非金融部门去杠杆带来的有效需求不足,私人部门信贷增长乏力抑制通货膨胀的上行。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火索是房地产资产价格泡沫的破灭,对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导致了居民长达十年的去杠杆。本次疫情是通过居民就业渠道影响居民的收入水平,疫情期间居民收入靠财政补贴没有明显下滑,但疫情过后可能出现的企业破产以及就业市场结构性转变给居民收入带来的持久性影响,也会抑制短期居民和企业的加杠杆,这意味着短期总需求仍会较为疲软。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疫情对居民资产负债表冲击影响的时间长度将会低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这也提升了未来通货膨胀上行的概率。
●压制通货膨胀的结构性因素依然存在
根据前述分析,展望未来,压制全球通货膨胀的结构性因素短期内都难以缓解。
第一,防止全球贫富差距的扩大需要全球进行收入再分配改革,对各国来讲,改革都将困难重重。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加剧了民粹主义思潮,也增加了全球政治经济的不稳定性,不过,即便各国政府考虑完善收入再分配,这也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第二,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盛行,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会加剧逆全球化思潮。未来全球化只是改变了一种形式,全球产业链会有所收缩,全球贸易将更加区域化,但各国不会将所有的产业回流,区域化的贸易和分工不会大幅增加一般消费品的成本。
综上分析可知,疫情过后,虽然非金融私人部门大幅加杠杆的动力不足,但其资产负债表所受到的冲击要低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这会缩减未来通货膨胀低迷的时间,全球性通货膨胀有望归来。不过,考虑到压制全球通货膨胀的结构性因素依然存在,会压制通货膨胀反弹的高度。通货膨胀的长期预测一直充满着不确定性,尤其在美联储平均通货膨胀目标制下,通货膨胀会如何影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操作,也将变得更加不确定,未来通货膨胀将成为金融市场较为关注的一个变量。
(作者单位:陈骁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魏伟、郭子睿为平安证券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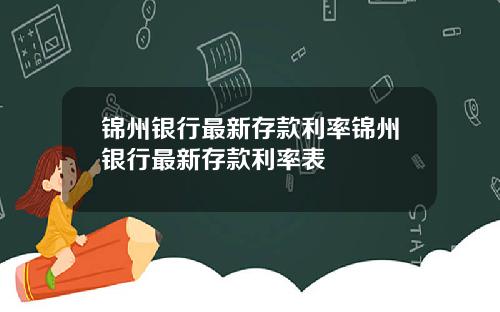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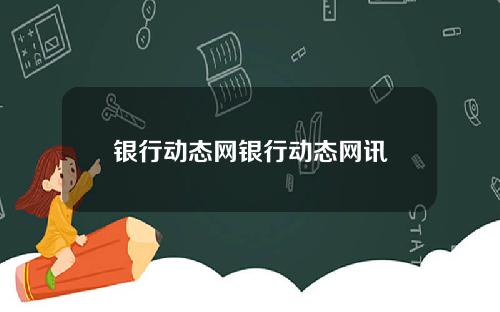
.jpg)